
“三弟,醒醒啊!”
“你若出事了,我们可怎么办啊?”
吵!好吵!
季清越既觉吵闹,又觉头痛欲裂,对于萦绕在耳边的声声“三弟”更是恼怒。
什么三弟?她是女人!
借着这股怒意,她终于掀起了沉重的眼皮子,视野有些模糊,但很快,两个有些憔悴但难掩美貌容姿的女子映入眼帘。
似乎看到她睁开眼,离得近的那位穿绿衣衫的女子尖叫了一声,刺得她耳膜发疼。
“我、我去请大夫,姐姐你好好照顾他!”
穿着桃红色衣衫的女子擦拭了眼泪,应了声,小心翼翼的看着季清越,“三弟,你可还有哪儿不舒服?”
季清越心想,我哪儿都不舒服,软绵绵,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。但目前最要紧的,是她的身份。为什么两名女子穿古装?她躺在古香古色的床上,以及,自己什么时候成了男人?
“水,给我水。”
她强撑着要坐起来,吓了桃红色女子一大跳,“好好好,我给你拿水,你别动,乖啊!”
说完,她就匆匆忙忙的去倒水。
季清越借机观察这间屋子,突然间视野充斥着大片阴翳,大股记忆被塞入脑内,她的头又痛起来,只能躺回去,浑身痉挛起来。隐约间,她听到桃红色女子的尖叫声,还听到绿衣女子的争辩声,质问为何不能去请大夫,最后是一道有些沧桑虚弱的女音。
昏过去之前,她想,这都是些什么事啊?她不过是在值班的时候打了个盹,怎么就遇到这么诡异的事情?应该是梦,对,就是梦,睡一觉就好。
结果,在梦里她经历了一个同叫季清越的短暂一生。
季清越,生于大周朝熹明六年,父亲是账房先生,母亲相夫教子,家庭算是和睦,唯一不好的一点是,父亲一族连续多代单传,一心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,光宗耀祖,甚至成了心病。
老大季璎出生时,他算是高兴,颇宠爱大女儿。老二季珞出生时,他就有些郁郁寡欢甚至开始酗酒了。老三,也就是她,又一个女儿出生时,季父直接疯了。疯癫几个月后,突然认定季清越是男儿身,给了双名不说,还大肆宣扬。
母亲顾氏软弱,又怜惜季父,便真将季清越当做男儿养,告诉她一些男儿该注意的地方,甚至尽量避免她外出见人,以免被外人发现。季父甚至在家给他开蒙,后来还请了先生,一心要她参加科举。
因为季父的坚定,顾氏的顺水推舟,还真的没人发现季清越是女儿身。包括接受了十几年男儿教育的季清越,都觉得自己该参加科举,光宗耀祖,担当起照顾家人的重任。
四年前,顾氏还有两个月要生产时,给她看诊的大夫告诉她,这一胎是男孩。顾氏欣喜若狂,握着季清越的手说要帮她恢复女儿身,不参加科举,一家人搬到其他地方去。
然而,当时季父就在门外,听到这一切,受到刺激,发狂出走,溺亡。顾氏受到惊吓早产,多年来缠绵病榻,幼弟亦是体弱多病。
季清越真的成了家里唯一的“男子”,需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。
随后梦境里就是顾氏卖嫁妆和小院,举家搬到京城,一家五口开始过着贫苦的日子。走马观花里,多是季清越和顾氏决意豪赌一场。季清越入太学刻苦学习,参加科举,一路到殿试,成为二甲,被赐进士出身,后赐官大理寺评事,从八品。
消息传来,季清越欣喜若狂,比话本里的范进中举后疯了还要可悲,直接一命呜呼,换成了她这个现代之人。
原身的情绪是如此的浓烈深沉,几乎让季清越以为,那是她活过的十六岁,那是她的不甘心。
再次醒来时,屋内已经点了油灯,这油应该不是什么好油,熏得她眼睛有些疼。
还是那个破旧却很有古韵的房屋,而她床边,只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美貌妇人,难掩病容。
这是季清越的母亲——顾氏。
察觉到她醒来,顾氏立马颤巍着手要扶她起来。
“阿母。”
开口的那瞬间,季清越就红了眼眶,这是原身的情绪。顾氏却立马上前抱着她哭泣,“我的儿啊,为何偏偏是你受这个苦!我的儿啊!”
悲极伤身,见顾氏都要上气不接下气了,季清越阻止了对方的哭诉,“阿母,我没事,休息一晚,明日我就上任。”
季清越本身就很有主见,她应该在很多事情上和顾氏达成了一致,因此顾氏只是伤怀,情绪有些复杂,“你没事了再上任吧,大理寺那边应该不碍事。”
“没有必要闹特殊,皇上赐官因为让很多人注意到我了。”
季清越以自己只是太过喜悦而晕厥说服了对方,在目送顾氏离开时,她微笑的说,“姐姐那边由我来解释,您不必担忧。”
顾氏背对着她的身体一颤,随即沙哑着嗓音应下了。
关于不能请大夫这件事,原因在于大夫只要把脉,就会知道她是女子。因此自小有个头疼脑热,都是顾氏拿着药方去买药,而不是请大夫上门。好在多年来季清越身体算是康健,没有生活大病,就这么熬过来了。
当然了,和两位姐姐解释时,她的理由是,“我只是一时大喜,休息会就好。别以为你们不告诉我,我就不知道家里只剩下三天的粮了,哪来的钱请大夫?”
顾氏当年卖房子卖嫁妆,举家搬入京城,租了外城一破旧两进小院,又想方设法送她入太学,花了不少钱。四年里一家五口的吃喝住行以及她的学费书本费,母亲和弟弟的汤药费,家里的钱能够支撑到她过殿试再被赐官,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- 1
- 2
- 3
- 4
- 5
- 6
- 7
- 8
- 9
- 10
- 查看更多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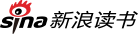





 去书城逛逛>>
去书城逛逛>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